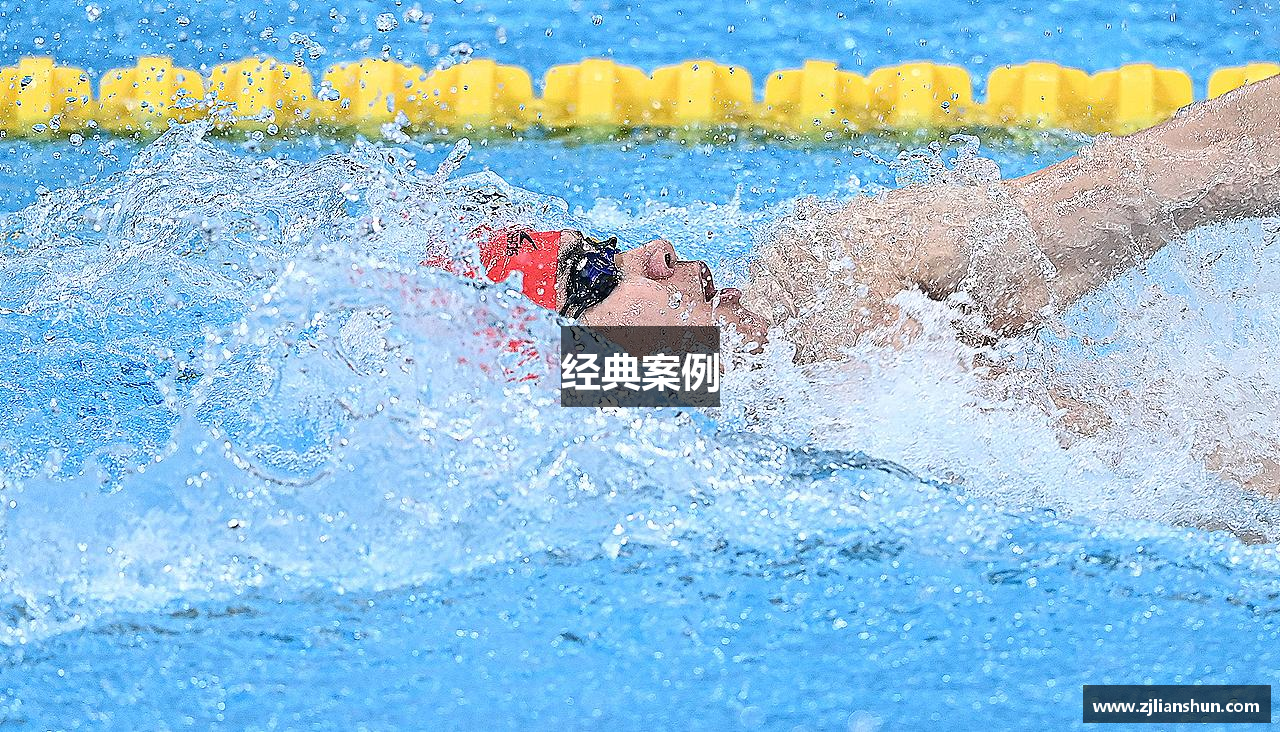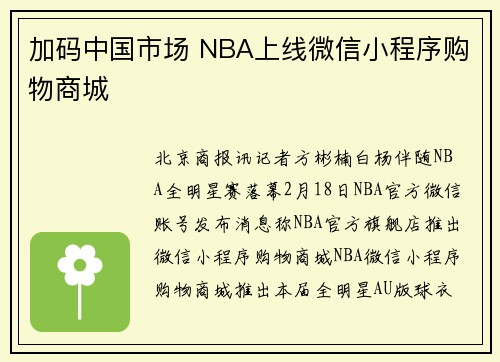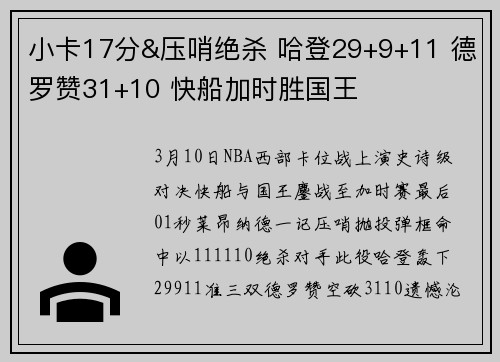参观都江堰、三星堆与成都平原
乘着老人腿脚还算便利,乘着孩子还愿意跟我们出门同行,每年我都会带老人孩子旅游度假。今年选的地方是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我们参观了青城山、都江堰、三星堆和杜甫草堂,深感成都平原文化积淀之深厚。从青铜器时代的古蜀文明,到战国时期的治水工程,东汉以降的道教文化,以及唐代以来的诗词书法,一路行来收获满满,大饱眼福(及口福),也令我思绪万千。其实我到访成都的次数至少已经三十次,但是基本都是工作和授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悠闲地参观游览,更没有请了导游仔细讲解过。
大奖国际先说三星堆。三星堆到目前为止还在发掘之中,不断有惊喜。古蜀文明的神秘、辉煌,令人文社科学界广泛关注,也充满想象和期待。我是一名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票友,根据导游的讲解和我自己参观中所见实物,并结合目前已经公开的情况,我对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特质有着以下理解和猜想。(请注意,以下都是基于我自己非常有限的那点历史地理和人文知识所做的猜想,而非专业见解)。
首先,古蜀人在人种上似乎并不是网上传播甚广的中东白人,他们的凸眼珠、高鼻梁,其实只是宗教活动中的面具。当然,也有可能是当时的蜀地普遍缺少碘盐,有一小部分人因此而出现眼珠凸出的长相,而这种长相在古蜀宗教中被解释为神性的表现。
其次,来自西南地区的象牙和印度洋的贝壳,某些带有明显中原地区商朝风格但是却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丰富的丝绸稻米产品,接近西南民族传统的建筑格局,这些都说明古蜀人跟东方的长江流域、北方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云贵、缅甸地区,都有着活跃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由于古代的交通运输能力的限制,这些联系并非后来的繁荣贸易和深度分工,而是偶有使节和工匠人员的往来以及由此带来的礼物、技术和知识的传播。由于长江支流和秦岭的隔绝,使得这个文明跟西南方向的联系很可能比东方更加精密。
再其次,这应该是一个神权至上的文明,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教权(巫权)似乎与政权高度融合,并汲取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凸显神的权威和至尊。这种宗教显然不是一神教,神山、神树、神龙、神鸟,都是太阳神崇拜体系的一部分。太阳神崇拜在古文明中非常常见,在阴雨连绵鲜有晴天的成都平原,喜欢和崇拜太阳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们在宗教活动中大量运用黄金、象牙、玉器和大型青铜铸件。精美的工艺品制作技术显示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是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在铸件或者玉器上刻写文字符号,所以暂时无法确认古蜀文明是否有成熟的文字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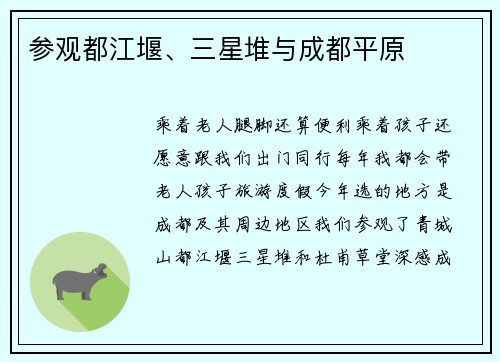
最后,我在听导游讲解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既然古蜀人崇拜太阳,而又有很多山峰的符号出现在青铜器上,那么他们的祭司很可能会在成都附近的某座高山之巅设有大型的祭坛,其中必有大型的青铜神树。古蜀国灭亡之后,贵重的祭品比如金玉可能被人捡走,但是青铜器陶器之类的残片应该还有不少。逻辑上讲,这样的祭祀之处应该在三星堆的正东或者正西方,或者东西方都有。
三星堆文明何时消亡?是否一直延续到公元前四世纪?这个问题有待考古专家和史学家的回答。假如这个三星堆文明如我所猜想的那样一直延续至2400年前的古蜀国(其间的一千多年未必是同一个政权同一个统治谱系,但是族群大概率是能延续下来的,某些宗教文化传统也能大概率保持下来),那么这个文明古国在公元前316年被商鞅主政的秦国所攻灭。论幅员和人口,古代的秦国应该与古蜀国不相上下。但是,两个政权和社会的组织模式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以神权来维持民众的顺从的青铜器文明,另一个则是春秋战国的乱世中逐步演化而成的以耕战为本的法家国度。一个神神道道地长期内卷、靠天吃饭,而另一个整天则想着入关,问鼎中原。当然,要想吞并关东中原诸国,必须先获得翻倍的实力,于是并吞巴蜀地区便成为秦国扩张成长的第一步。剑阁是中国地缘战略史的一个重要关卡,的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国战争史上在此发生过很多故事。但是,地利之便不足以抵挡赳赳老秦的战略雄心。秦灭巴蜀之后,才有了百年之后的李冰开山治水的事情。
阿坝地区的高原雪水汇成岷江滚滚东流,却由于地势的原因,对成都平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岷江出岷山山脉后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是地道的地上悬江。成都平原的整个地势从岷江出山口玉垒山,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都江堰距成都50km,而落差竟达273m。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所以,李冰治水成功,使得成都平原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去不返,岷江从一条恶龙变成成都平原的丰产守护神。
我早就在书本上看到过都江堰的示意图,但是直到身临其地,目睹飞沙堰、宝瓶口和离堆的精妙设计,才真正明白李冰父子数十年治水中惊人的智慧、胆略和想象力。说得通俗点,就是用人力把大山打开一个口子,把山南的岷江江水分出一部分到山北流入成都平原,然后用大量的人工河流在平原上编织出一张水网浇灌农田,从而改变这个地区的水土条件,造出一个旱涝由人的天府之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用百度地图仔细看看都江堰和成都平原的水文分布。在此不再赘述。
治水是中华民族的一项种族技能,(与之可以类比的可能是种菜)。当然,治水是国家层面的事情,集中力量办大事,短期内重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换取长期的政治经济战略收益。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背后是人定胜天的决心、信念和历史记忆。秦国除了派李冰在蜀地治水搞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在其他多个地区开展类似的投资,最有名的比如郑国渠。
农耕时代,一个地区能够养多少人,主要取决于其耕地面积和质量,尤其是取决于其荒年灾年的粮食产出。李冰父子治水成功之后,成都平原从一个相对闭塞的落后地区,迅速变为秦国东向晋地、南出楚国去争霸天下的粮仓和兵源地。如果有历史学者从事那段历史的研究,不妨从各种史料中寻找相关数据,推算一下成都平原人口总量和粮食产量的在都江堰建设前后的变化。
我觉得可以如此理解成都平原从化外贫瘠之地变成华夏体系西部粮仓的历史意义:秦国之所以能在后来历经数轮大战而不断取得决定性胜利,以一灭六,除了在制度和治理等方面有其特点外,还离不开成功夺取并开发了巴蜀地区这一战略侧翼。
从后世来看,不仅是秦国因为巴蜀而得天下,历史还不断地重复此逻辑。秦末战争中刘邦因为掌控巴蜀而经得起与项羽的消耗战,刘备占得巴蜀而有资本同魏吴争锋,一直到元末明初,巴蜀仍然具有割据为独立王国的潜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汉中一定要划在陕西,剑阁不能成为两地之边界,从而降低蜀地分裂割据风险。